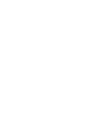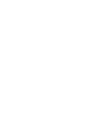流放后,我在敦煌当汉商 - 第71节
“贱名好养活,名字贱命不贱就成了。”腊梅嫂子看着白白净净的小丫头,说:“依我看,你家这丫头不如叫阿水,水是干净的。”
老牛叔若有所思。
又有人来看孩子,老牛叔大方地让人看,有人不怀好意说孩子不像他,他乐呵呵地笑:“不像我才好,姑娘家,长丑了说婆家的时候遭人嫌。”
一个没牙的老头怀里抱着个没牙的婴孩大大方方站在巷子里任路人围观指点,不论是话里藏针还是语里带刺,他都装聋作哑当没听明白,衬得心怀恶意的人面目丑陋。到了后来,口出恶言的人少了,毕竟是一个刚满月的小丫头,她跟谁都无仇无怨。
没有等到隋玉回来,小丫头先饿哭了,老牛叔抱着孩子回去吃奶。
佟花儿喂奶时,老牛叔坐地上看着,他低声说话:“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藏着躲着避着人,都随你。但你不能压着我闺女也缩在家里,我堂堂正正领回来的,她就能堂堂正正走出去。我都不在乎她长得像哪个男人,你在乎什么?”
佟花儿轻轻“嗯”一声:“我晓得了。”
“我今儿得了个好名字,阿水,我觉得好听,以后我丫头就叫牛阿水。”老牛叔说。
佟花儿没意见。
听了老牛的一番话,佟花儿隔天就抱着阿水走出家门,虽说是出了家门,但她也不跟谁交谈说话,时不时在隋玉住的巷子里晃一趟,或是往远处走。
隋玉打草的第五天碰到佟花儿,两人在巷子口走个脸对脸,谁都没说话,对看一眼各走各的。
但不过一日,佟花儿就带着老牛叔找去隋玉打草的地方。老牛叔少只手打草不方便,再加上他也懒得干活,他就在一旁负责抱孩子,佟花儿拿着镰刀下地割草,再摊开晾晒。
孩子饿了,她就坐在地上奶孩子,孩子吃饱了,她就继续割草。
两亩种着金花草的沙地,隋玉跟隋良在南边割草,佟花儿一个人在北边割,两方能看见人,但都不说话。
老牛叔抱着阿水走到隋玉那边,说:“四头骆驼,你今年要准备不少干草。”
隋玉点头,“这两亩还不够,好在之前我用骆驼运了一亩的豆杆回来,若是再不够,只能等赵西平回来想办法。”
说罢,她抬头往对面看,说:“老牛叔,你带婶子回去,打草是个轻省活儿,我跟隋良忙的过来,不用她帮忙。”
“她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来干活也好,免得她抱着孩子四处乱晃。”老牛叔怀疑佟花儿是在打听隋灵的消息,他可不想惹麻烦,如今她愿意来打草,他再没有不情愿的。反之帮忙劝隋玉:“你就当没她这个人,你们各忙各的。”
之前阿水洗三隋玉没去吃饭,佟花儿就明白她的意思,此次她虽然来帮忙,但绝口不跟隋玉说话。
每天不吭不声过来,赶在隋玉回去前又不吭不响的离开。
属实是各尽各的心意,不谈过往的恩怨,更不涉及帮忙了就要求谁原谅谁。
金花草晒干,隋玉搓了四筐草绳来捆干草,用骆驼运回去时,佟花儿就在门外等着,两人一个递一个堆,干草的高度一点点堆过院墙。
“隋玉,你俩之前认识啊?”对门的婆子操着一双三角眼来回打量,她试探着说:“这人平时谁都不搭理,却日日帮你干活,你俩是亲戚?”
隋玉没承认,不必要多添是非,她说是自己雇的。
干草都运回来后,隋玉这下轻松了,之后的日子她背着弓箭去收割了庄稼的地里寻找田鼠和野兔。
头一天,隋玉射中了一只田鼠,她拿去十七屯送给老牛叔。
第二天,隋玉往远处走,她追着一只野兔进洞,在洞外守了半天没守到。
隔天她不死心又过去了。
这次遇到了隋文安,他也是来打野物的。
隋玉皱了下眉头,她衡量着要不要离开。
隋文安先一步走了,他改去西城门,递交户籍后,他出城寻找猎物。
傍晚时分,胡大人听小厮说隋文安又给隋慧送来一只野鸡。他派人找来留意隋文安动静的村长,得知隋文安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四处打猎,猎物除了给隋慧送来就是换钱买面,攒了粮就蒸包子往长城根下送,次次去次次挨揍,伤好了还会再去。
胡大人敲着手指仔细咂摸,良久,他开口说:“不用盯着他了,以他这副优柔寡断的德行干不成什么大事。”
第75章 带话给隋玉,让她改嫁
经过半个月的追踪,赵西平一行三十个人在酒泉以北的马鬃山山脚发现了流窜的匈奴行踪。
刚一碰面,两方就打到了一起。
流窜的匈奴性子凶恶,身量高壮,驭马技术精湛,在力量方面,疏于训练的汉兵卒不及他们,唯有手上的武器持有赢面。
赵西平被安排在后方发弓,四箭射中两人,先后两人从马背上栽下,匈奴心生警觉,打斗过程中避开发箭的方向,甚至是扯着汉军做遮挡。
箭筒里只剩五支箭,赵西平望着烟尘弥漫的搏杀场,他持弓久久找不到射箭的目标,他感到吃力,不得已,只能驱马靠近。
隐在一墩石头后方的匈奴贼悄无声息冲向马背上的弓箭手,在即将靠近时,赵西平猝然回身,绷着皮弦的手指一抬,锋利的箭簇穿胸而过,穿着兽皮的匈奴贼砰然倒地。
一柄弯刀砸来,胯下马匹受惊,四蹄前奔,连累马背上的人骤然后倾,险些摔下马背。赵西平连忙拉住缰绳,就在他手无空闲时,后方的匈奴骑兵手持砍刀追了上来,一个探身,弓弦挑断。
匈奴大笑,盯着赵西平如即将丧命的猎物,满眼的狰狞。
赵西平顾不得多想,他从马背上抽出长刀,错身时挥刀砍马,贼马吃痛惊蹄,马背上的匈奴人翻身下马。
赵西平打的就是这个目的,他马术不精,在马背上拼杀,他毫无胜算。
不远处,敌我双方厮杀到关键时刻,赵西平回看一眼,他手握长刀背负箭筒下马,迎上面目阴沉的匈奴贼。
两刀互砍,铮的一声,两人足下互踢,肩头互撞。赵西平咬牙大叫一声,他一侧身,抽刀挺出胸膛,拼着胸口挨刀,他举起长刀在砍刀的刀刃划破皮肉时,奋力一斩。
人头落地,随后砍刀也砸落在地。赵西平喘着粗气以手捂胸,鲜血从指缝争相流出,滴滴啦啦落在扬尘的黄土地上。
伤势不要命,赵西平忍痛撒上药粉,他唤回黑马,拽着缰绳翻身上马,手持卷刃的长刀返回搏杀的战场,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尸体,鲜血压土,扑起的灰尘落了许多。
赵西平打马绕圈,帮落在下风的战友砍杀匈奴贼,一旦有人放弃目标朝他追来,他就纵马狂奔,不跟匈奴人正面迎上。
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时辰,正午时,以三个匈奴贼带伤落跑为尾声结束了战斗。
山脚下血气大盛,马蹄带起的灰尘在秋阳下徐徐升空,砍伤大胯起不来身的健壮马匹卧倒在地声声嘶鸣,空中鸟雀盘旋,山腰上狼嚎阵阵。
赵西平撕裂外衣靠在石头上处理伤口,兔毛坎肩已被鲜血浸透,挡住刀刃锋芒的木板早已四分五裂不知去处,鼠皮裂痕下的伤口血肉翻滚,鲜红的血正从伤口中滴落。
“呼——”赵西平长呼一声,他忍着心惊从地上的死人身上翻出伤药敷伤口,药粉撒在伤口上,他疼得额头冒青筋,待痛感褪去,脸上起了细密的汗珠。
“怎么样?”武卒垂着砍伤的膀子走过来。
“死不了。”赵西平擦了擦血,他感叹说:“匈奴人力气不小。”伤势比他预想的严重。
“吃肉的肯定比吃米面的力气大,这次伤亡又不少。”武卒心生后怕,又闻一声狼嚎,他打起精神,说:“影不影响赶路?我们收拾收拾该走了,等天晚了,山上的狼要下来。”
赵西平坐着不动,说:“让我缓缓,不影响赶路。”
“行。”
武卒去清点伤亡的人数,赵西平背靠在石头上心有余悸地看着,距他半步远的地方就躺个死人,他记得他的名字,顾世成,是个挺胆小的汉子,这次出门是被他老爹塞进队伍里的,只因他老爹想让他练练胆子,没想到出来一趟就没命了。
如今儿子没命了,顾老爹估计下半辈子都活在愧疚里。
赵西平想到了自己,他摸了摸砍破的坎肩,若是他死了,隋玉就是活着,下半辈子也不好受。
“你杀了四个人。”武卒提着一串人耳过来,以对账的口吻掰算:“射死三个,斩落一个人头,其他还有没有?”
赵西平摇头,之后他都是补刀,算不上单独斩获。
“行,上马吧。”武卒甩了甩人耳上的血珠子,指着旁边的尸体说:“你带上顾世成,往北走个两天,寻个好地方给埋了。”
赵西平没意见,他扶着石头起身,突然想到什么,他跟武卒说一声,俯着上半身往远处走,捡回掉在地上的藤弓。
搬运尸体的兵卒捡起一柄完好的弓箭扔给他,说:“这不是有完好的,你拿一柄回去,回去了跟校尉少报一柄就是了。”
“我习惯了这把弓的重量,回去再续一根皮弦就是了。”赵西平没要,他将藤弓从包袱缝塞过去,继而扬唇一笑,炫耀道:“这把弓是我媳妇送给我的,能在战场上保我的命。”
其他人闻言同时“嘁”一声。
凝重的气氛陡然松懈下来。
来时三十个人,回去时只余十三个活人,十七具尸体绑在马背上,再杀死哀鸣不止的伤马,每人取坨马肉,带上俘虏的贼马和贼人抢来的砍刀、菜刀、粮食、布匹、皮毛打马西去。
五人带伤,回程的速度慢了许多,天黑露宿时,远处的狼嚎清晰可闻。
背风坡的空地上堆起个火堆,火光照亮每个人的脸,架在火堆上的马肉有了香味,不知谁的肚子咕噜一声。
武卒戳着油光发亮的肉坨递给赵西平,一走近就闻到了呛人的血腥味。
“伤口又裂了?”他问。
“嗯,歇一晚估计会好点。”赵西平虽然饿,但没什么胃口,他抽出刀放火上烤了烤,削一片马肉喂嘴里,说:“我要是不带伤,这会儿能再返回去射杀两头狼。”
“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想出息。”武卒嗤一声,“下次还出来?”
赵西平毫不犹豫地出声:“出来,我回去再好好练练箭法,拳脚也要练练。”
“鬼迷心窍。”武卒不屑。
可不就是鬼迷心窍,赵西平没反驳,他轻按了下伤口,伤得这么重,他怕的要死,竟然还不打退堂鼓。
夜深了,夜风在山间呼呼作响,赵西平抖开狼皮盖身上,他躺在火堆边闭眼睡觉。半夜被冻醒,他感觉四肢无力,头脑发沉,浑身倦怠得让他没精神。
“我发热了。”他推醒武卒,“有没有什么药?”
武卒转醒,他掏出药又给赵西平重敷伤口,伤口敷好,他拿来一囊烤热的水递过去,又去检查另外三个伤兵。
睡前精神不错的三人都有些发热。
“天亮后,先送你们去附近的城镇看大夫。”武卒说。
赵西平躺在地上看夜幕,他有些担心,伤口引起的发热比狰狞的伤口更要人命。他想起了隋玉,他要是死了,她怎么活?
半夜煎熬,天亮后,一行十三个人上马,翻越山涧循河而上,走出马鬃山,远远能看见酒泉郡的城墙。
晌午时,赵西平等人走进一座城外小村,村里有个游医,煎几碗药给他们灌下去,又让他们趁早去城里的医馆看大夫。
武卒决定不再带着尸体上路,他派五个人先带赵西平等人去酒泉郡,他跟另外两人留下来挖坑埋人立碑。
夜幕降临时,一行十个人抵达城门外,递交手书讲明情况后,城门一侧的小门开了,赵西平等人连夜住进医馆。
割肉清创、施针、喝药汤,赵西平迷迷糊糊感觉到疼。
再醒来已是两日后,他睁眼觉得面前站的妇人眼熟,看了好几眼,才试探着喊:“娘?”
赵母冷笑一声。
赵西平隐隐觉得不妙,他打量下环境,还在医馆里,只不过不见其他人。
“娘,你怎么在这儿?我那些同僚呢?”
“我来看看我的痴情种儿子死没死,阎王殿的老爷夸没夸你?”赵母见他醒了,兜手打他一巴掌,“老娘怎么生了你这个憨东西?你贱啊?为了个女人不要命了。”
赵西平沉默,他在心里骂武卒一通,指定是武卒漏了口风。
赵母掐腰大骂一通,见他板着个脸装聋,越骂她越气。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