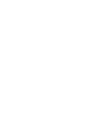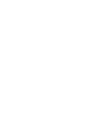恋人是人外(1v1) - 【极夜花火·其十】
手帐翻开一面,笔尖悬停在纸上,犹豫再叁,迟迟不能落下。
阮秋秋端坐桌前,独自陷入沉思,她有满腔情绪等待倾诉,想要把那些复杂的、焦躁的以及难以言说的暧昧想法宣之于笔,然而千折百转之后,它们却纷纷停滞不前,积郁在指尖处,不肯写出一字半句。
就这样干耗了大半钟头,纸上依旧空空,仅有几条细碎短线,无法组成连贯字体。
腰肢隐隐开始酸软,她起身活动身体,神情略显疲累。并非源于昨夜那场性事的激烈过程,而是安德烈的怀抱实在灼热紧迫,哪怕挣开些许空隙,下一瞬又被牢牢缠绕,尾巴缚住双腿,不容半分推脱。阮秋秋在夜半睡得并不安稳,直至清晨对方离开,才算彻底放松。
在床上浑浑噩噩消磨了半日功夫,等她走出卧房时,居然已过晌午。
简单洗漱之后,阮秋秋便呆坐桌前,她在雪原中被迫养成记事的习惯,总结每日单调生活,哪怕再乏善可陈,她也总能寻出一点琐碎,可在今天竟是个例外。
阮秋秋直勾勾看着空白书页,踌躇着不知如何记录荒唐。
一切都乱套了,从那个吻开始。
如同引燃一线火花,怦然炸裂之后,满天余烬覆盖全身,形成斑驳颜色。
不知是否错觉,当视线落向那些深浅交错的吻痕时,阮秋秋甚至能感受到些许燥热,恍惚回到昨夜相拥之时,蜥人嘴唇在肌肤上游走,不断舔舐吸吮,触感粗粝而不失温柔。
耳垂随即开始发烫,他的亲吻正如未灭的焰舌,哪怕只是稍稍回想,仍然可以灼燎周身。
意识到这点后,阮秋秋连连摇晃脑袋,努力将那些靡乱画面一一甩出,想要从这格外羞耻的心猿意马中脱身。
从厨房接过一杯冷水饮尽,冰凉液体涌进胃部,让她稍稍获得清醒,于是打定主意先做点别的事情,以免胡思乱想。
阮秋秋取出放在卧房里的那迭照片,每当感到寂寥时,她都喜欢翻阅这些东西,画面远比文字更具表现力,能够直观的通过它们回忆过往经历。里面大半是沿途所摄,余下部分则是食物,记录着日常变化,偶尔穿插几张白塔室内陈设,气氛冷硬简洁。
而那张辗转两次的照片正摆在其中,阮秋秋没有费心私藏,而是一齐摆进箱柜里——她笃定安德烈不敢擅自闯入卧室翻查,虽然这本就是他的房间。
说来也是好笑,安德烈似乎对它仍旧念念不忘,时常暗自到处找寻,有时被她瞧见,又要强抑慌张假装无事发生,模样十分有趣。
思及此处,阮秋秋忍不住又起了作弄心思:假使让他知道相片是被自己故意取走,会是什么反应呢?
念头一闪而逝,很快遭到了否决,安德烈性格虽是寡言隐忍,却经不起丝毫挑逗,她可不想再度体验引火烧身的滋味。
值得庆幸的是,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种族壁垒深刻,这片大陆不乏异族结合,然而诞育子嗣的案列极少,天然的生殖差距阻隔了混血降生,因此无需担忧事后的紧急避孕措施。在阮秋秋接触过的同性中,有一部分格外青睐异族,仿佛形成了某种特定趋势,在体能长度与无风险的加持下,他们成为了最佳炮友选择。
实话实说,这也是昨夜阮秋秋愿与他共度的重点原因。
但……她与安德烈算是这种简单的床伴关系吗?
心思一浮,手上动作同时滞涩,相纸哗啦散落开来,打碎她的一腔疑虑。
阮秋秋不得不重新整理归纳,忽然留意到手中握着厚厚一迭,仔细数了数,居然累积了近百张。似是想到什么般,她翻开手账追溯日期,才愕然发现自己来到高兰已逾两月。
真是漫长,她原本有些感慨,可转念一想,又觉两月时日过于短暂,短得让人来不及捋清所有情愫,就先迈入欲望旋涡。
实在是太仓促了。
年轻的姑娘趴在桌前,手指死死绞住发梢,就此跌进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
这份纠结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伴随安德烈的晚归,终于抵达至前所未有的高峰。
她盯着指针向下缓缓推移,已然远超平常回家时间,枯坐良久之后,才将桌前微凉的晚饭端进厨房重新加热。
除了那夜检修电器,安德烈向来准时,是在哪里耽搁了吗?
偏偏自己的手机坏了无法联系,偏偏事情又发生在今天。
无数猜想恰如蓬蒿恣意丛生,她一面毫无缘由的担忧揣测,一面孩子气般迁怒食材,不断按压锅铲,肉块被粗暴分割切碎,浓郁的酱料香气在高温中散发。
为什么偏偏是今天?
难道他是有意避而不见?
阮秋秋垂下长睫,抬手抚向额心,那里残留着一枚轻吻,正是相拥一夜后,蜥人临走之时特意遗下的。她在浅眠中感应他的温存,却不敢声张回应,唯恐激起涟漪。她隐隐畏惧这份波澜,只好选择避而不见,退至禁区以外。
但这举动并不高明,晚间安德烈便会回来,届时又该怎样面对?总不能一味装睡蒙混过去,阮秋秋为此预想了无数种应对方案——可眼下对方压根没有回来,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脑子顿时像是裹了层厚重浆糊,与食物一道被丢进热油里来回翻搅,除了杂乱无序的滋滋声响,再整理不出别的头绪。
而在愁与疑的交替中,她心心念念的蜥人同样被阴霾笼罩。
安德烈正身处于白塔底部,陷入原地呆立状态,因紧张而迟迟不敢回屋。
越是眷恋昨日缠绵,就越是担忧今天相处,经过整夜的转侧难眠,自然积郁了满腹烦躁,连一向适应的工作都变得难以忍耐,他总觉莫名饥渴,体内怪物时刻逼迫着要他奔去温暖所在,寻求一点甜蜜慰藉。
然而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他反而开始徘徊不定了。安德烈想象着阮秋秋的神情反应,那张娟好面庞或许浮现恼怒,又或许染着幽怨,却总不会是带笑的。他知晓昨夜一切起于迷乱,对方甚至可能感到后悔——人类素来保守排异,与一名外族发生关系可谈不上什么好事,何况还是他这类危险存在。
掌心传来阵阵麻痛,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双拳过度紧握,四指深陷掌心,好在尖利指甲早被削去,又隔着厚厚手套,不至于割破皮肤。
于是安德烈一面松开拳头,一面反复模拟各种见面说辞,直至炽烈的思念烧灭了耐心,使他终于硬着头皮迈入顶层,在机械沉重的开合声响中向上挪进。
一阶一阶踏得虽是艰难,但安德烈心里到底是存了些不切实的希冀,盼着她的眉眼依旧温和如水,平静等候他的归来。
然而当他抬首望向旋梯尽头时,却没有见到那道熟悉的逆光身影。
只这一霎眼的功夫,安德烈便莫名感到疲累,像是被剥离了浑身气力,张了张嘴,呼吸竟也显得滞塞。他扶住护栏缓冲许久,又强撑着拖动躯体,才浑浑噩噩走回居所。
室内景象远比往日清冷,客厅开了一盏小灯,素来温馨的暖调也变得灰暗,昏昏照亮角落里那一方餐桌,上面空空如也,假花独自端丽盛开。
茫然环顾周遭后,酸涩猛地攥住喉头,连同鼻腔乃至胸口,上下剧烈撕扯。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安德烈还是为之怔忡,他望着卧房那扇紧掩的门扉,沉默片刻,慢慢坐回沙发,任凭外衣风雪凝化水珠,滴滴答答落在地面。
蜥人垂下头颅,牙关死咬,鼻息反而愈发粗重,山岳般的身躯轮廓剧烈起伏颤抖,呼出的热气却好似消散在极远处,在那莽莽暴雪之中。
……最糟糕的猜测得到验证,她甚至不愿意见他了。
就在安德烈即将承受不住这份痛苦倾轧之际,一束亮光忽地落在身上。
厨门被人拉开,油烟气息乍然四散溢出,脚步声由远及近。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她的声音柔柔落下,柔的仿佛挂在白云梢头,以至于安德烈一时间无法反应过来,维持着僵硬姿态。
阮秋秋则被他这幅模样吓住,慌措地捧起对方脑袋,想要探究原因。玄关处传来的熟悉动静早就传入耳里,她知晓他的归来,却迟迟不肯出面迎接,一边慢条斯理抚平衣衫上的褶皱,一边犹豫该摆出什么表情来,好让对方知道她的不满。
她原本想着,一定要使点小脾气,不需吵闹,但得表现出足够恼意,让安德烈以后别再随意晚归,至少跟她知会一声。
在这片荒芜之中,她不得不紧紧系扣着他,化为菟丝,化作寓木,以此尽可能攫取安全感。
然而屋外的异常令阮秋秋放弃佯怒打算,贴着房门聆听半晌,只有沉寂作为回应,她赶紧推门而出,谁想竟瞧见安德烈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
疑惑冲散了眉间的浅浅愠色,她又低声问询了一遍:“是不是不舒服?”
安德烈这才确认眼前的真实,下意识朝那双温暖掌心贴去,他躲在防护外罩之下,声音含混而委屈:“有点累了,所以坐着歇会,没事的。”
阮秋秋不再多说什么,动作熟稔的替他解开那身湿濡外罩,注意到那根长尾萎靡垂下,便将他的脑袋重新捧住,朝自己怀里贴去。
两人姿势陡然间亲近无比,她尝试抚慰这只陷入莫名哀伤的大蜥蜴。
安德烈手臂无措地抬了抬,不敢落在那截腰肢上。他躲在怀抱之中,小心翼翼用面颊蹭了蹭娇软小腹,焦虑感迅速崩塌瓦解。
阮秋秋的手指掠过蜥人头上细密沟壑,围着后颅不断打旋,这能引发他的舒适放松。绕着绕着,她听见掌心下的呼吸渐渐恢复规律,于是轻轻开口:“还在不开心吗?”
这话倒起了反效,他将头埋深了些,额头抵上胸乳,不带狎昵意味。
灶火带来的食物油气盖过了她本身的暖甜,但安德烈并不在乎,他沉溺于如今的安心氛围。那些酝酿已久的腹稿统统作废,他哑声解释起来:“我以为你生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阮秋秋眨眨眼眸,故意提高音量,掩饰心虚。
“……我碰了你。”
隔了好一会,安德烈才给出答案。
“那我昨晚就该生气,你把我的内衣都给撕坏了,讨厌的很。”
阮秋秋嘴上似在抱怨,笑意却从眼底溢出。心底腾升出一股窃喜,原来对方也同自己一样,在不可见的角落里患得患失。
幸好她素来机敏,稍微回想一番,轻易找出了症结所在,“我刚才忙着热饭呢,你回来的这么晚,都等了好一会,菜也凉了。”
不可否认的是,期间她虽有心冷落,但也确实为安德烈的归家而欢欣踏实。这份感情许是源于朦胧好感,许是因为他们相互依存,可阮秋秋不介意将它袒露,索性凑向耳孔轻声细语:“我正高兴你能回来,你呢?你也高兴见到我么?”
话音落下,她的腰身被外力猛然束紧,蜥人那双坚实臂膀终于环覆上来。
“高兴的。”他说。
“骗人,你让我等这么久。”
阮秋秋咬住唇瓣,刚想抽身推开,长尾颤颤勾上脚踝,粗粝鳞甲来回摩挲肌肤,不愿放任她的离去。
“今天是去外面巡视,以后不会再晚归了。”安德烈为自己的敏感多心而感到惭愧,羞于启齿真正原因。她若是知道了,一定会笑话自己的。
“还在落雪吗?”阮秋秋问。
他点点头,视线飘向别处,“很大的雪,还要一阵才能停歇。”
“这样啊。”阮秋秋闻言,失落之余,又莫名松下口气——她曾有过一闪即逝的离开念头,尽管听起来颇为可耻,甚至充满逃避意味,如同事后翻脸不认账的渣男做派,但她深知只有早日告别高兰,彻底回到正轨,才能规避泥足深陷的境地。
安德烈当然不是污沼,他更接近于死寂火山,会在某个节点骤然爆发,将她汹涌吞没。
第六感叮叮咚咚敲响警钟,催促她做下决断,可当对方委屈巴巴的倚靠过来时,阮秋秋就把一切抛之脑后,只剩了满腔柔情婉转。
会不会有点恋爱脑?不对,明明还没和他谈恋爱。不对不对,为什么要设想谈恋爱?
阮秋秋有些控制不住脑瓜里的小人打架,生怕被他看出端倪,慌忙仰身退后,却被牢牢限制在臂弯当中。
雄性的干燥气息蔓延,隔着衣料,高热体温再一次燎动着她。
安德烈随之抬起头来,由于身形魁伟的关系,即便保持坐姿也能与她平视,红瞳端端对上面庞,他在缄默里投来深深凝望。
约莫是视线过于灼烈,紧密纠缠一路,阮秋秋不禁别过身子,脸颊晕开层层绯色,几乎染透眉眼。她低声问:“我脸上有东西吗?”
对方旋即否认,语调带着罕有的吞吐,“有一点红罢了。”
话音落下,安德烈就开始后悔——他本想进行夸赞的。
女人的侧影浸着橘色,沾染柔和光晕,周遭微尘恍如星屑,以她为中心萦绕运行。无疑是极美的画面,他却难以用言语详尽描述,笨嘴拙舌地憋出一句脸红,实在不像样子。
阮秋秋赧然似的掩去半张面孔,只露出明媚浅亮的褐瞳,朝他轻哼:“你也是。”
“你怎么知道?”安德烈下意识反问,他天生的黝黑皮肤足以掩盖所有异样。
“不知道呀,瞎猜的,看起来我是猜对了。”阮秋秋说着,眼尾翘起弧度,只觉这段对话分外幼稚,与他的行为一样,莫名冒着傻气。
身前蜥人闻言,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竟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好笑,垂头发出一阵模糊笑音。
说来奇怪,本该是场尴尬会面,毕竟情欲冷却后的清醒时刻最为难堪,可两人相处依旧暧昧,潮润黏稠的欲念充斥在表象之下,又被另一种怦然而青涩的悸动所取代。
“秋秋,我……”
气氛愈演愈烈,安德烈情不自禁向她贴拢,正要开口,忽然嗅到一股若有似无的焦味,沿着角落蔓延而出。
两人动作随即凝固,在他调头看向厨房之前,阮秋秋的惊呼声打破了所有旖旎。
“——哎呀!菜糊了!”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