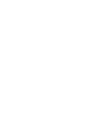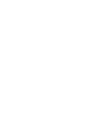镇国公主[GL] - 镇国公主[GL]_分节阅读_133
镇国公主[GL] 作者:允
我心中大动,既是异常欢喜,又是异常担忧,踟蹰良久,方下定了决心,等李睿与韦欢退开,李旦亦被人抱下去之后,自上前牵着母亲的衣角,轻声道:“阿娘,儿…有话禀报。”
母亲本已有些疲惫地靠在了御座上,听见我的话后微抬了眼,手搭在扶手上道:“你阿兄出京之事已定,若要求情,就不必了。”
我在御座前跪下去,仰面看她:“不为二郎之事,是为了阿娘。”
母亲偏了头,饶有兴味地看了我一眼:“你说。”
我手心里捏着汗,慢慢道:“阿娘改立三郎,虽是为国家社稷而废不肖、立正统,然而三郎年纪毕竟是小了些,阿娘总务万几,未必能事事照料得到,若有万一,恐怕朝中不稳。”
新帝初立,我实在不该说这不吉利的事,可阿欢从前连些许小事都不肯借我的力,如今却求我将她留下,我不可不为她尽心竭力——何况留下她又正合我心中那点猥琐的愿望?
母亲凝视着我,我知道她在以打量臣下的目光看我,以小女儿的柔顺姿态将头贴在她的腿上,轻声道:“二郎毕竟是阿娘唯一的儿子,朝中不可能没有任何异议,更何况还有故冀王府及东宫僚属,此是一;裴炎等出身世家,位列宰辅,如今又预废立之事、行社稷之谋,威名既赫,权耀当时,此是二;高祖封建,遍布宗室于四海,辈分高者有霍王、鲁王,功高者有嗣齐王、宣城王,亲者有许王、郢王,有贤名者有泽王、舒王,此是三——这三者都是朝中威胁,倒不是说他们必有不轨事,不过新帝初立,母后临朝,正是朝中兴废的紧要时候,不可不防。且三郎虽经母亲册立,毕竟不是先帝亲生,生父又是先帝时便废黜之太子,若有人真要以此为由,另行拥立,亦是一害,阿娘不可不三思。”
往常我若做这样亲昵的举动,母亲总要抚抚我的头,或是拍拍我的肩,今日她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片刻后方道:“继续说。”
我道:“先帝至今留有二子,濮阳王自先帝时便遭贬斥,又是庶出,与其子皆不足为凭。二郎是先帝所立,名分最正。诸孙中,唯守礼是二郎之子,奉节是大郎嫡子,二子最为紧要。奉节已后,唯守礼名位最尊。二郎既已年长,又是被废黜之君,不可使留京城,守礼年幼,却可与大郎和濮阳王诸子一道养育宫中,以备万一——儿所说一切,都是阿嫂无子时的情形,若是阿嫂有子,自然又以她的儿子为尊。”停留少顷,才说出最后的话:“儿以为,为母亲和二郎计,二郎该当之国,阿嫂和守礼却该留在京中。”将一切说完,心中反而坦然了,退开一步,伏身在地,敬候母亲的裁决。
母亲过了很久才慢慢开口,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你觉得阿娘照料不好三郎?”
我怔了怔,不自觉地抬头看她,却见她已经自御座上起身,长长的裙摆拖曳在地,覆盖住了自御座至我之前的大半地面。我想起阿欢,竟将诅咒当今圣上这事做得异样平静:“儿知道阿娘疼爱三郎,必将竭心照料,只是这世上祸福谁也难料,三郎年纪这样小,若有万一,阿娘总要有防备的。”在地上一顿首,以极轻的声音道:“晟哥已经去了,睿哥也离了京,阿娘留着旦儿和守礼,只当他们…还在身边罢。”
母亲又没有说话了。我仿佛看见有一滴泪自上滴落,摔在母亲的裙摆上,偷眼看时,却见她只是眼角微红,面色依旧如常,站了好一会,终于弯了腰,伸手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他们此时多半已出了城,你和独孤绍骑马去,将守礼和你阿嫂追回来。”
这是将人情留给了我。我应诺一声,刚一起身,听见母亲又道:“让殿中选宫人姣好者二十人,及朕宫中春桃、公主府中楚儿、韦玄贞第三女,一并送至庐陵,侍奉二郎。”
这话不是对我说,我却也躬身听了,看见婉儿自暗中出来,向门外走去,转头看母亲,她已走回御座,闭眼靠坐在上。
我缓缓地退了出去,到门外僻静处打开手中留藏的飞鱼银盒一看,只见十片指甲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艳红颜色,如宝石般闪耀人眼。
作者有话要说: 网页有问题,存稿箱打死存不进去,于是直接更新了…后天早上七点准时更_(:зゝ∠)_
…………………………………………………………………………………………………………………………
小剧场:
太平:你送什么不好,送指甲是几个意思?
韦欢:这还不懂?想上公主的意思呗,笨。
太平:……
…………………………………………………………………………………………………………………………
第178章 心疼
李睿一行出了城便在驿站住下,因此独孤绍与我追得倒并不费力。押送的校尉先接出来,过了好一会,才见李睿战战兢兢地自驿中挪出,看见是我,长舒一口气,似有无数话要说,最后却只唤一句“兕子”,抹去眼角的泪水,低声问:“太后还有什么吩咐?”
他被废之后,倒是迅速成熟了,见我与独孤绍同行,立刻便知这是母亲的意思,我,踟蹰片刻,到底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便利落地道:“传陛下口宣:朕以飨亲致孝,欲厚人伦,着庐陵王妃韦氏、子守礼,恩留宫中,宜奉慈亲,用伸孝道。庐陵王仍往藩地,宜加抚慰,当体眷优。”说完不敢看李睿,只拿眼看韦欢,却见她面色不变,低头起身,吩咐七七:“抱大郎下来。”
有乳母将守礼带下来,小家伙已然入睡,两只小手伸出襁褓,肉鼓鼓的,极是可爱。
韦欢的行李几乎便未打开,等我们传了令,直接将东西一搬,带着两名宫人,与李睿道别。李睿此刻方回了神,惨白着脸道:“阿娘…”
我心中生出些许内疚,握着他的手道:“阿兄放心,有阿嫂在京中,你那里消息不至断绝,若有什么事,阿嫂与我,也可为你挡上一挡。”这倒是实话,李睿听了,面上却并不见欢喜,转身将韦欢一看,叹一口气,将她的手也握了一握:“宫中凶险,日后要辛苦你。”
我再想不到李睿能说出这种话,拿眼去看韦欢,韦欢垂了头,将手从李睿手中抽出来,淡淡道:“二郎放心。”
李睿眼中又滴出泪,伸手抱了抱守礼,亲将他交在我手中,又牵着韦欢的手交在我手心里:“兕子,你阿嫂和侄儿,总要托赖你。”
我心上人的丈夫将她和她的儿子托付给了我。不知为何,我竟有些想笑,嘴角动了动,未及说话,独孤绍在旁催了一句:“天晚了,走罢。”方将韦欢和李睿的手放开,翻身上马,与独孤绍及宫中禁卫一道护送着韦欢入了宫。
天的确是已晚了,母亲命我们两在绫绮殿暂住一夜——想不到我们分开几近一年,最后却因为这样一个巧合又住在了一重殿中,我心中未免生出些荒谬的感觉,然而再是荒谬,毕竟我们又在一起了。
这一晚上等人都入睡以后,我便起身换了衣服,仙仙觉出我起身了,起身要问,被我嘘了一声,便识趣地坐回去,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悄悄踏出偏殿,绕着内殿回廊去了韦欢所在。
母亲待她倒算宽和,并不严兵把守,宫人们则因她身份,反倒更加懈怠,她那里除了两个正在门口打瞌睡的小内侍外,悄无一人。
今时不同往日,我谨慎地在她门口徘徊片刻,又摸到窗下,正打算探听里面是否有人,却见那窗户的缝隙中露出一张脸来,韦欢要笑不笑地从那缝里看我,手推窗格,低声道:“进来。”
我便熟练地挤进窗,翻进内殿,里面只有七七一个侍儿,也早被韦欢打发到外间,偌大殿中,不过我们二人而已。
我不由自主地便抱住了她,在她耳边叫一声“阿欢”,她亦回抱住了我,轻轻叫一句“太平”,不多说话,只有眼泪默默流下,沾湿了我的肩头。我本有无数的话要和她说,被她这无声之泪一催,却也只是叹息流泪,半晌方抬头,擦了泪,心里怪她莽撞,又有许多疑惑要问,想她乍逢大变,倒不好催逼,便只低声道:“阿娘的意思是从宫中选出一道地方,改造为‘百孙院’,所有皇孙都住在一起,你和守礼亦不例外。我想过了,宫中只有近掖庭宫的地方还适宜,且离前朝和正寝又远,你们多半是住去那里。我明日便在修德、辅兴二坊置第,若你们真搬去那里,只要遣人出掖庭,到我第中送信,我即刻便知,我若有信,也叫人送到那里,你派人去取就是。”
韦欢不答,只两手环住我,不住盯着我看。
我自初尝□□,于今已旷乏了近一年,被她这样搂着,便觉周身荡漾,难以自持,又顾忌着外面,便两手推她:“好好坐着说一会话,说一会,我便回去了,如今是非常之秋,阿娘心里忌惮二郎和守礼,我们都要处处小心。”
韦欢却还不肯松手,被我催了几次,方慢慢松了手,垂眼道:“你替我办了这样的大事,却连一句话都不想多问么?”
我何尝不想问她?然而如今回想,其实一切都早已明明白白,根本没什么可问的。
当初我们倒都想到过这事,我亦曾殷切嘱咐,叫她务必留心,她却一味只说她心中有数,我则是习惯使然,想着她这样聪明有主意,既说了有数,自然就是有办法的,且心里也以为母亲必是属意守礼,多半是学那北朝拓跋氏的旧例,迫李睿做个太上皇罢了,她拿准了守礼这筹码,我则依赖着她,结果我们两谁也没有真正上心,事到临头,慌张凌乱,真是活该报应。
不过话说回来,纵然我们两个一开始便知道母亲要立奉节,也根本无可奈何。母亲之于我们,不啻泰山之于丘陵,韦欢再是聪明绝顶,也不过是初生小犊,怎能和母亲这持国秉政数十载、又占着礼法大义的太后相比?以韦欢如今的身份,私下里投靠母亲,只怕母亲还嫌她不够分量,让她活着随从李睿、带着宫人内侍和行李之国,说不定已是天大恩典,不信看看从前的太子妃裴氏,便知如今的韦氏,已是何等幸运了。
其实这一两日间发生的事,说起来惊心动魄,载于史册,亦足以为后世反复提及,可是对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眨眼间的事:邱神勣鞠问李晟时,母亲便已暗暗派人将李晟诸子带回京中,等李晟死讯一传开,就召了裴炎,聚百官和皇帝于太极殿。李睿被叫去时还以为是为的李晟之死,坐在殿上,红着眼圈,开口便是“二郎可谥节悯”,结果母亲叫人将他拽下座去,把写好的废帝诏书一宣,再将奉节抱到御座上一坐,百官朝拜,这事就结束了——听说李睿直到被叉出殿外,还在问“我何罪”,殊不知他在这时做了皇帝,便是最大的罪过。可笑的是当日母亲已拟定了李晟的谥号“昭肃”,追封他为雍王、赠开府仪同三司的诏之后以新帝的名义下发,就在李睿被赶出去不久、太极殿中。
自事后来看,这些事真是清楚直白得如同白纸上斗笔写的黑字,可是事先却绝少有人能料到,连早知道历史的我也一样。
母亲能做到日后那个地步,的确是有许多不同寻常的手段的。而我们所能做的,唯有默默忍耐,等到这一段历史过去,下一段历史来临。只不过属于我们的那段历史也并不长久,很快我们便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变成史书上简单勾勒的几个名字。因我们是女人,多半连名字都不会有,我是“高宗第二女封长乐公主”,她是“某宗韦皇后”,或是“庶人韦氏”,身份高低,全看命运他老人家的心情。
我什么话都不想问,我只想静静地看一看她,抱一抱她,守着这难得的、独属于我们的片刻时光,品啜这独属于我李太平,而不是高宗第二女、武则天爱女的感情——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地方去,乖乖地做我的长乐公主。
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韦欢自己蹙着愁眉,却伸手来抚我的眉头:“小小年纪,皱个眉做什么?早早地皱成了老妪脸容,当心驸马嫌弃你。”
我按住她的手,眉头皱得越紧:“你明知我喜欢你,何必又来说这样的话。”无论是“小小年纪”,还是“驸马”的话,在这种时候提起,都令我很不舒服。
可她偏偏要提:“正因你喜欢我,我亦喜欢你,所以不忍见你这样自作自贱,驸马他丰神俊秀,是出名的美男子…”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